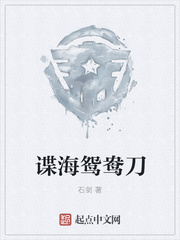草海之文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太子拓跋晃监国,见寇谦之、崔浩迷惑父皇信奉道教,出于逆反心理,就********信奉佛教。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众大臣晓得拓跋晃是后来的人主,也就纷纷信奉佛教,有的居然在家里蓄养和尚,讲经说法。崔浩历来鄙视佛教,称其为胡教,认为佛学荒诞不经,念经侍佛耗费时日,消耗资产。拓跋焘又借鉴后秦姚兴信奉鸠摩罗什,西凉蒙逊供养无谶和尚而导致两国皆亡的教训,下令各家户口皆不得私养供奉和尚(当时寺庙还未兴起,和尚大多托钵行走,或由家庭供养)。过了二十五天的限期,还不将和尚清除出境的,诛杀满门。如此严厉的命令,一时在北魏兴起了一股灭佛的风潮。也是佛教该有此业劫,此时盖吴在长安造反,拓跋焘亲自率队镇压,部队在长安郊区驻扎。一支小分队就驻扎在一所庙边。此时正是初春严寒,这所寺庙的主持见了驻军,为讨好小队长,就请小队长进寺庙喝酒御寒,小队长在庙里喝酒,看见庙里收藏有很多种兵器,一出庙门就立即将庙里的情况报告了拓跋焘,拓跋焘下令部队包围寺庙,收缴兵器,对一个个哭丧着脸的和尚说:“兵器不是和尚的道具,你们必然是和盖吴一伙阴谋造反的叛匪!”下令将全庙的和尚一律斩杀,庙产充公,一把大火,将庙宇烧为平地。就这样,拓跋焘还不解气,一概把和尚定为叛匪,在全国不分老幼,一律坑杀,连塑造泥人菩萨的,铸造铜人佛像的都满门抄斩。全国上下,一片灭佛之声。躲藏在平城的大和尚,面对此劫难,纷纷招纳各地真传弟子,往太子东宫躲藏。太子拓拔晃笃信佛教,也没考虑其利害关系,只是为了做好事,就收藏了各地的高僧名梵多达几百人。北魏灭佛,佛教僧侣纷纷逃往江南避祸,为南国的佛教兴盛埋下了伏笔。
灭佛事件极大地打击了东宫的势力,权力天秤的砝码尽被司徒崔浩掌控。为了加快北魏汉文化的速度,崔浩提任官员一概由汉官担任,而将原任拓跋部族的官员予以罢免。这小小的官员任免事件终于成为其后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线。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
年)二月,拓拔焘平定北方之后,为完成统一大业,决定南伐。拓拔焘御驾亲征,率领十万大军南下,攻打刘宋。魏军攻打的第一个目标是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县)。拓拔焘命令部队从东、北、西三面攻城。刘宋守卫悬瓠的主将是左军参军陈宪,守城的士兵不满千人。魏军昼夜攻城,制造几十部高楼车,士兵在楼车上往城里射箭,矢下如雨。守城士兵或者披着棉絮,或者张开鱼网,犹如诸葛亮的“草船借箭”。拓拔焘见箭矢无效,又命令楼车上用大钩牵楼堞,毁坏南城。陈宪是知识分子型的将军,办法多,又在南城内设女墻,外立木栅以拒之。拓拔焘始终无法,只得老老实实攻城。拓拔焘命令填平堑壕,肉搏登城。陈宪督厉将士苦战,城墻下堆积的尸体已经和城墻一样高,魏军士兵乘尸上城,短兵相接。陈宪身先士卒,奋勇当先,将士们以一当十,浴血奋战;守城将士死亡一半,魏军更是死亡一万多人。战斗整整进行了四十二天,战无不胜的拓拔焘没想到会在小小的悬瓠城碰到颗硬钉子,又听说刘宋派来援军,包抄魏军退路,只好暂时撤军。
北魏太武帝出征期间,崔浩任命冀、定、相、幽、并五州郡守,太子拓跋晃任命的郡守全部被罢免,而由崔浩精选的汉族知识分子担任。这些被罢免的拓跋族官员灰溜溜地回到平城,都去太子东宫哭诉,指责崔浩擅专朝政。太子拓跋晃找到崔浩,据理力争。说:“先前征派的州郡人选择,都是些在职已久,勤劳问政的干部,所以才提升为州郡牧守,崔公你新征的人选,应该在各州郡、部曹历练几年,或为属员,或为副职,其后提升才是,你这一来,完全打乱了我的部署。”
崔浩蛮横地说:“我以司徒之职,任命委派吏员,这本来是份内之事。况且,这五州郡人选也已经上任,就这么办好了。”拓跋晃在灭佛和官员任免这两次事件中和崔浩的较量都失败了,心里很不舒服,回到东宫,即招集拓跋部落的望族大户旧门阀,罗列崔浩的罪状,向皇帝告御状。太子去到皇宫,却没见到皇帝,拓跋焘开春后又到东郊狞猎去了,还要两天才能回来。拓跋晃心生一计,又刊列崔浩一条罪状,命人表奏太武帝。然后对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说:“圣上对《国史》暴露国恶一事十分震怒,要追究你们几个著作者的责任,高公要免祸,唯有将责任全部推到崔浩身上,到时候我才好帮您说话。”高允没想到太子这么关心自己,噙着眼泪点头应允。
太子拓跋晃闻讯,急忙带着高允去向皇帝请罪。拓跋焘因《国史》事件正在气头上,一见到高允就指着他的鼻子怒骂:“朕命尔等撰修《国史》,想不到尔等连朕的祖宗三代都骂了个遍,你们这不是饱修国史,而是暴露国恶。你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高允也是个忠直耿介的“笔头公”,跪在地下不卑不亢地说:“秉笔直书是史臣的职责,没有谁指使我,‘国史’都是我一人撰写的,微臣这是秉承良心,尊重事实,书就千年信史。如果圣上认为不妥,要剐要杀,都冲着我来!”听了高允的话,父子二人都大吃一惊,没想到大臣中又出现一个“笔头公”。拓跋焘气得无语,好半天才哆嗦着说:“好,好好!算你狠,你是个硬骨头,朕饶你不死!”太子拓跋晃见事态完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赶忙启奏说:“众所周知,国史并非高允一人所为,崔浩身为总编修,罪在不赦。况且将国恶丑事勒石铭立,置之于通衢大道,糜费国家资财,沾污先祖形象,皆他一人所为,理应由他承担责任。”拓跋焘好半天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个字“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