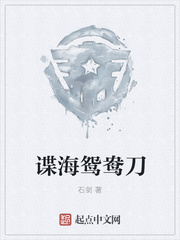草海之文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田奇回到建康,向刘义隆汇报了拓拔焘的提议。一听拓拔焘首先让步,南宋只须送上女人质,表示自己和亲的意愿就行了;有这种好事,江湛一流的大臣都纷纷表示赞成,只要北魏能退兵,做出怎样的牺牲都是愿意的;反正是割别人的肉,痛苦不在自己身上,让皇帝老倌也尝尝妻离子别的滋味儿吧。志大才疏的太子刘劭可不愿意妹妹成为和亲的牺牲品,在殿堂上大闹起来:“不行!他拓拔焘是什么东西,胡虏小竖,我刘氏皇家可没有那么多的女儿再当第二个王昭君。”江湛害怕太子坏了和平大事,急忙对宋文帝说:“女子和亲,换来长久的和平,这可是双赢的局面。”刘劭厉声说:“什么双赢。当年就是因为你鼓动北伐,结果引狼入室,魏军百万大军南下,弄得山河破碎,六州沦陷,似这样的罪过,必须得有人承担责任,只有斩江湛以谢天下。”江湛是皇帝的最爱,刘义隆怎么舍得杀他,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急忙出来打圆场,说:“北伐原是我的决定,与江爱卿无关,你就不要怪罪他了。”刘劭见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老爸还一味袒护江湛,再也不愿多言,气冲冲的下殿,走到江湛身边,故意狠狠的一撞,差点没把江湛撞倒在大殿上。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会议,就这样在大臣们各逞口舌之能的争吵中不欢而散,没有一点实质性的结果。
幸好,田奇的外交手段胜过百万雄兵,特别是那句“佛狸死卯年”的谶语给拓拔焘造成浓厚的心理阴影;不然,南宋的政治闹剧也许要就此谢幕。腊月三十这天,拓拔焘实在无法排遣心中的郁闷,独自徘徊,好不容易打到长江边,眼看就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没想到时不我待,天不假年。明天就是辛卯年春节,拓拔焘可不愿像诸葛亮那样“出师未捷身先死”,毙命客途他乡。他信任的崔浩、寇谦之都不在身边,他对预言一类的谶语又深信不疑,弄得整天忐忑不安。拓拔焘步出军营,登上瓜步山,望着脚下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心潮起伏。当年,魏武帝曹操为了统一中国,曾发兵几十万南下,与不堪一击的孙刘联军展开激烈的赤壁之战,胜利本来是毫无悬念的,没想到最后却铩羽而归。更有最近的苻坚,为了一场“投鞭断流”的喜剧,饮马长江;结果,最终演出的是“仓皇北顾”的人生悲剧。拓拔焘可不愿步曹、苻二公的后尘,暗暗萌生了退兵的想法。拓拔焘东临瓜步,以观长江,本想赋诗一首,以记今日之盛,而江风徐徐,却吹不走他一腔愁绪,那里还有心情作诗。最后望了一眼长江,转身离去。公元
年春节,拓拔焘在瓜步山上大宴群臣,封赏有功将士,征求大家的进退方案。每逢佳节倍思亲,众位将军出征半年,都想回家团聚,尽都愿意退兵。独不傲众,拓拔焘无奈,只得同意撤军。当天晚上,魏军沿江点燃火把,庆祝胜利,东西绵延七十里,以此示威。火把燃烧到第二天,魏军把长江北岸洗劫一空,将千万家房屋付之一炬,百万大军,回师北去。
战争结束,田奇的甜言奇语,即退百万之军,确实功不可没。这个当代的蔺相如没有得到一点封赏,田奇无怨无悔。可是,自此一仗,南宋的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尽成千里赤地,万具白骨,一片荒凉,百里萧疏,大好的“元嘉之治”,显现出衰败的景象。
魏军回师路上,又来到盱眙。既然已经休战,魏太武帝为了表示友好,送上精美的刀剑,请沈璞赠送美酒。没想到盱眙主帅此时换成了臧质,礼品都落到了他的手中。臧质此人是典型的官二代,他是臧皇后的从子,虽然此人是败军之将,却照样被委以重任。这家伙打仗不行,搞恶作剧是一把好手,听说拓拔焘要美酒,就用酒坛子装进“美酒”送了出来。拓拔焘满怀高兴地斟酒即饮,没想到喝进一口臭尿。拓拔焘一摔酒杯,下令攻城。两军交战,比的是智慧勇武,以溲代酒,这哪是一个职业军人应有的做法。好在拓拔焘无心再战,若此时挥戈南下,突然袭击,说不定会踏平南宋的都城建康;那时,臧质才真的成了千古罪人。北魏军队在拓拔焘的指挥下,向盱眙发起疯狂的进攻,士兵们抬着钉板床攻城,声称要活捉臧质,让他受活罪。可是,毕竟盱眙城里有文武双全的沈璞指挥抗战,魏军苦苦战斗了一个月,丢下一大片死尸,盱眙城毫发无损。初春乍暖还寒,死尸腐烂发臭,瘟疫流行,士兵们大多染病,战斗力锐减。战争要诀:先三天锐,后三天钝,再三天笨。面对蜗牛一样的士兵,拓拔焘又气又闷,又无法扫除“佛狸死卯年”的阴影。一十天,又十天,再十天,盱眙城久攻不下,拓拔焘的心理阴影越来越浓,无奈之下,不得不命令撤军。
又气又闷的拓拔焘回到平城,对自己制造崔浩哄动一时的冤案十分后悔,暗暗责备自己太过冲动,酿成了这场大祸。自崔浩伏诛以后,此时,拓跋焘才静下心来,思前想后,感觉到太子奏章中的猫腻,为表达自己的愤怒,收回了太子监国的大权,又亲临朝政。皇帝的率意而为,众大臣从拓拔焘的言行中嗅出了对太子不信任的味道,落井下石的人纷纷在太子身上寻找突破口。皇帝重新执政,深为可惜的是,依之为肱股的崔浩已经不在,人死又不能复生,而身边再也没有崔浩可以咨询,不得已找来李顺的从弟李孝伯作议政参谋。宣城公李孝伯在征战南方时虽有上佳表现,却连一句谶语都无法解释,自然没法和司徒崔浩相比较。不久,年事已高的李孝伯在征战南方时身染重病,此时传来病重的消息,后来又传说李已亡故,拓跋焘在宫中哀悼李孝伯,说:“李宣城可惜。”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对大臣们说:“朕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这无异于当众为崔浩平反。可悲啊,人已经死了,平反恢复名誉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平反又总比不平反好吧,至少为其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