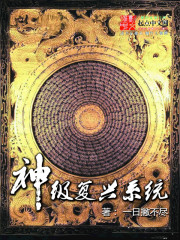Uusi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阿姨说,桃子家新屋建好时,屋前屋后种满竹子,年年冒出很多新笋,长成了个密挤的竹林。桃子要家人割下新笋晒笋干,晒好拿去镇上卖。也收获几个买布做衣的钱。
阿泥回来奔丧那天,阿姨正好在桃子家和容婶一起剥竹壳、烧水灼笋片、再摆到竹筛里晒笋干。是容婶叫她来帮忙的,帮一个上午,换五根笋和几角钱。桃子对竹笋过敏,碰不得,从没干过晒笋活儿。她摘菜去了。
容婶听见狗吠,一瘸一拐从灶房走出去。看见阿泥撸了撸黄狗头,拍打一下它的前臂,要它让路给他进屋。
虽然阿泥因建筑工作繁忙,请不到假,回来这天,阿金已经下葬一周。但骨肉无恨,见到儿子,容婶只剩下激动。可又像大部分农村妇女一样,把激动压抑掩饰起来,用不以为然和些许抱怨的神情迎接他。自然又为阿金的死捶胸顿足了一翻。
阿泥没那么矫情,他进屋就把一沓十几张一两元的纸币甩给容婶,叫她别哭了。他把他的前景描绘给容婶。他问容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改革开放?容婶说八九年前听公社干部说过这个词,但具体改革开放是搞什么的,她不知道。
阿泥耐心解释:“改革,嗯,改革就是,就是——比如,以前集体耕田,后来分开单干,这就属于改革的一部分;开放——开放就是香港同胞、台湾同胞、外国佬等等,可以进我们国家开工厂。加起来就叫‘改革开放’。我将来不用耕田也有饭吃。因为改革开放,广州南番顺一带,到处兴建高楼大厦和工厂。我是起高楼大厦的建筑工人。所以,我有了工作,大哥走了不用怕,我能挣钱帮补家里。”
容婶先是拍一下他的头,责备:“你大哥又不是一台拖拉机,没了坏了用别的代替就……唉,”
虽然阿泥意识到自己表达出了错,但他认为人实际上跟机器差不多。千万年来死那么多人,人照样延续至今,地球照样转得火热。
容婶责备哀叹后,问:“这么说你现在是工人阶级?有固定工作?”
“现在不讲阶级的啦。”阿泥说,想了想,懒得解释,干脆说,“嗯,我现在是工人。”
听到阿泥闯广州几年,从农民能闯成了工人,容婶也算得到些许安慰。
###
虽然阿金和桃子拜堂后即刻分家,他俩另起新灶。可建屋时经济不宽裕,得省砖省瓦,屋是一堂过,五间连体,另加两间小灶房。所以话说分家,还是门打开、低头不见抬头见。农活还是合在一起做,粮食还是合在一起收。实际,除了不同一张桌上吃饭,一切照旧。
阿金死后,父母又把桃子和孙儿合在同一餐桌上吃饭。
阿泥把装行李的蛇皮袋放到分给他的那间屋后。抓了一把糖果回到灶房,作为手信,递给那时还是个少女的阿姨。然后坐在餐台条凳上吃容婶给他端的面条,正吸溜着,抬头看见门外,桃子手里挎了个竹篮子回来。
桃子头上不再扎两朵好看的少女马尾。她天生一头微黄的头发,很厚很柔软,小时候头发里生很多虱子,阿泥常让她坐在门槛上,他站她身后,用篦子替她篦虱子。婚后,桃子把马尾编成了两条辫子垂在胸前。这是她唯一的大变化。
桃子的身段还是少女身段,还与没结婚前一样前突后翘得很玲珑。如果硬说添了什么,只添了少许被男人翻腾浇灌过的成熟韵味。
桃子不知道阿泥回来了。她把菜放在井边,进她屋去了。不一会,提了一桶脏衣服到井边洗。
阿泥继续坐在灶房里看她,她背对灶房门,折蹲着身子在井边,使劲搓洗摊在粗粝石板上的脏衣服。
阿泥想,桃子还是那个漂亮可爱的妹妹。
桃子全神贯注低头搓衣,没觉察阿泥朝她走来。阿泥走到搓衣石旁蹲下。桃子眼角瞥见人影,以为是容婶,没抬头,继续搓衣服。发际上细软的茸毛随她的搓洗一贴一飞扇动着。
“桃。”阿泥叫。桃子“咔”停下搓动,不敢相信地慢慢抬头看他。证实了是他,又千言万语化作微提嘴角一笑。她这一笑比哭还百感交集。
她和阿泥也不说话了,低头继续搓洗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