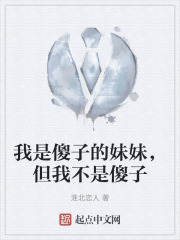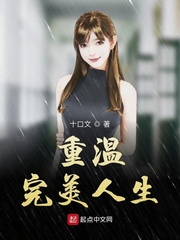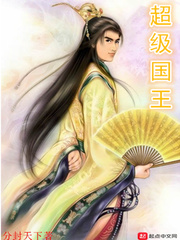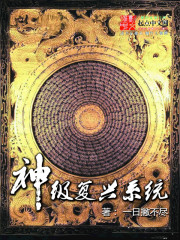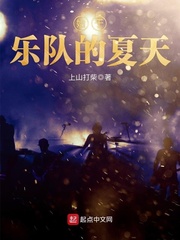Uusi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阿姨继续讲,
不知是县上还是镇上,调来了一支救灾队。
一辆解放军大卡车,载满
监狱的劳改犯,下灾区支援修路修桥。那些劳改犯可能是从城市押进山里劳改场改造的。他们站在颠簸起伏的卡车上,丫着嘴巴看穷乡烂屋。大概想,这些村舍已经够破烂的啦,洪水还不放过,硬把它摧毁成残檐断壁。
水灾又瘟疫,确实雪上加霜。
因为围龙屋是墙贴墙,梁接梁,瓦扣瓦,接成围龙的。一间倒塌,很容易牵扯拉倒邻墙。所以,洪水冲塌谢村围龙屋的百分之四十,却牵连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屋舍不能住人。谁都担心稍翻大风,落大雨,泥墙倒,瓦顶塌,会砸死人。
那些屋子全倒塌的人心里盘算,这屋连屋,烂屋修好了,以后再水灾,还是容易被牵扯倒塌,不如迁出围龙屋,另找地方起独门独户的泥砖瓦屋。但翻转枕头,数数存款,连买瓦的钱都不够。建新屋?想都不敢想了。
加上新换任的村长阿雄说,围龙屋是老祖宗留下的,农村有的是稻田泥,印些砖,把还能用的旧瓦收拾起来,再买少数新瓦,修楔结实,还能住上一两百年。
没钱,什么想法都仅一个“想”字。各村各户还是老老实实听村长的话,开始印砖(注释
)修屋。枕头下有钱的上山砍树,介木买瓦。没钱的也砍竹、割高芒草、削竹篾,建茅草屋。大部分农村人是没钱的。有钱没钱,总要整个栖身窝呀。毕竟不是鸟,枝头一站、树叶下一躲就能活下来。
这次大洪灾把我家和桃子家的屋冲塌倒到只剩下墙基。
我阿姆阿爸、老哑巴和容婶都翻出枕头下的存款,坐在干稻草上数。一分两分,最大面值一元,两家人反复手指往嘴里沾唾沫数,都数不够买瓦的钱。所以,能做的计划是先找块荒地,搭两间茅屋暂住。等筹够钱,再重建围龙屋里倒塌的两间屋。至于什么时候筹够钱,那是个未知数。
这次洪灾,让村里人比以往更强烈意识到钱比什么都重要。钱!哪能生钱呢?
来支援修路的劳改犯说,去广州打工嘛,改革开放了,那里建了不少工厂,没文化也可以进厂做手工。
八十年代初,村里便出现第一波涌出山,涌到县城,涌向省城的“打工仔打工妹”。
我和桃子也很憧憬大城市,很想走出大山,走向大城市。可那时我们才八九岁。能做的是天天掰手指数日子,希望过快些,好快点到拿身份证的年龄,拿到身份证就能去大城市打工挣钱了。
###
听阿姨讲到这,我记起我爸妈也说过,上个时间
年代初到
年代中,中国掀起一场“外出打工”热潮。许多农村子弟离开家乡,投身于陌生城市。这群人在城市释放他们的青春。城市的瓦屋变高楼,泥地变大理石地,天堑变通途等,一幕接一幕在神州大地上演。这史诗般的迭变有这群人的一份功劳。
而大城市里有文化的人,听说国外容易捞钱。能流国外的、也争着往国外流。我爸就是挤进流去海外的其中一滴水。当然,他只是公派去深造,两年后回国工作。
可后来他还是移民出去了。所以,我爸在外面稳定后,我妈放弃不知多少人垂涎的高中语文老师好职务,跟随我爸到海外生活。可每每,吃不到家乡食物、没朋友扯闲话、寂寞无聊时,就拿我爸出气,“你是思想非常不坚定的坏份子,见哪里好就往哪里跑的自私自利者!”
我爸自然很无辜,他当时也是想让我和我妈过好日子的呀。谁知道时运轮流转,转得那么快?八九十年代家乡还穷得路都不多两条。当时走出了山的人,头都不想往家乡方向回。可就那么二三十年的时间,逆转了!自
年国家出台多项扶持政策来,八九十年代涌出的“打工潮”,开始回流成“返乡热”。城市回家乡潮,海外回国潮。
我爸嘴硬,辩驳我妈,“我们现在生活得无忧无虑,快乐幸福,别贪心,回国竞争很大的。”
实际上他心里酸溜溜的,思念家乡的滋味。
###
阿姨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