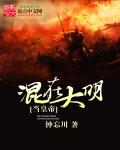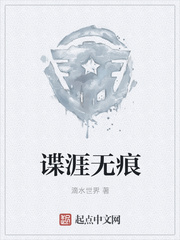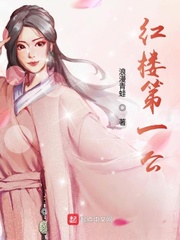曾鄫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第九十章 科举、国考(一)
江宁“三元及第”楼,这座有数百年历史的酒楼原本开张于前宋年间,据说前宋仁宗庆历年间,合肥的杨寘曾在此与高朋好友相聚一场,随后便高中进士第一名,加上他原本在解试、省试皆是第一名,真正的三元及第,于是给这座酒楼带来了无尽的荣耀和光环,并广为流传。嘉祐元年(公元
年),另一个合肥人-包拯知江宁府,听说这件盛事,于是便欣然题下“三元及第”。老板将其制成匾额,悬挂于酒楼大堂,于是这座酒楼便改称为“三元及第”楼。
靖康之耻,宋室南渡,“三元及第”楼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反而名声更噪,不少赴临安应考的举子都会绕道江宁,在“三元及第”楼吃上一顿,沾点文曲星的仙气。
蒙古入侵,山河沦陷,三元及第楼没坚持几年就关门歇业了,老板退回合肥老家过日子去了。直到刘浩然占据江宁,光复江南后,老掌柜的后人把那块深藏近百年的匾额又找了出来,并借着合肥老乡的名头在江宁城中另一处将“三元及第”楼重新开张,而且生意便一发不可收拾,但是都远没有这些日子来得红火。
三元及第楼有三层,人来人往举目望去大半都是赶来应试的秀才,几乎将楼上楼下所有的桌椅都坐满了。
一身便装的刘浩然坐在二楼的一角,丝毫不起眼,旁边坐的是冯国用和应天府知府陈遇、杭州知府潘庭坚。
陈遇,字中行,先世曹人。高祖义甫,宋翰林学士,徙居建康,子孙因家焉。遇天资沉粹,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初为元廷温州教授,已而弃官归隐,学者称为静诚先生。刘浩然据江宁,以秦从龙荐,发书聘之,引伊、吕、诸葛为喻。陈遇不日至,刘浩然与语,大悦,遂留参密议,日见亲信。
潘庭坚,字叔闻,当涂人。初为元廷富阳教谕,谢去。刘浩然驻太平,以陶安荐,征庭坚为刘府教授。慎密谦约,为刘浩然所称。下集庆,擢行省博士。东南势定,以庭坚行杭州知府事,以为东南重臣,这次他是受命护送东南杭州、湖州、嘉兴三府秀才前来应试。
“江南的学子菁华尽聚于江宁,多少年没有看到今日之盛况了。”
看到众多学子温文尔雅、持礼谦逊地互相打着招呼,他们都是一府一地的骄子,而且平时文诗相友、师门渊源多有认识,今日聚集在一起,都亲切地互相打着招呼,并向旁边的好友引见着,口里却是别人的字、别号和儒雅敬重的词句。看到这种情景,潘庭坚不由心有感慨,有感而发。
看到刘浩然眼中也有欣然之『色』,潘庭坚不由多说了一句:“此次科举一过,不但江南士人其心尽收,天下学子们也会心有所向。”
听到这里,刘浩然淡淡一笑,改指着桌面上的菜肴说道:“酒楼老板是合肥人,做得一手的好菜,大家来尝尝。”
冯国用在旁边接言道:“大家都来吃,尝一尝合肥地方菜的味道,品一品这处地灵人杰的风韵。”
陈遇和潘庭坚都笑了,他们知道冯国用的所指,合肥在前宋出过以铁面无私留名青史的包拯和历史上极为少有的三元及第杨寘,现在又出了一个刘浩然,这合肥当然算得上天宝物华、地灵人杰。
大家相视一笑,纷纷举起筷子,夹了一点自己眼前的菜,动作都非常斯文。虽然现在是微服私访,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三人在刘浩然面前还是不敢太放肆。细细嚼了几口后,陈遇与潘庭坚低头轻声说了几句,冯国用却坐在那里还细细地品味,甚至闭上了眼睛,似乎能从刚才简单的巢湖蒸鱼里吃出熊掌味道来。
刘浩然却在低头想着另外一件事情,自己是“伪合肥人”,祖父辈和父辈都在另外一个世界活着,而且据说自家原本不是合肥人,是在明初从湖广迁过来的,具体原因不知,所以说这祖坟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想来也发生不了刘伯温为自己迁祖坟,却发现是个风水龙脉的故事。
正想着,旁边一桌秀才们的争论声传来了过来。
“读书当是以程朱理学为本,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持圣人之德而教化天下。”一个白净无须书生气宇轩昂地说道,他的话得到了旁边众人的赞同,无不抚掌叫好。
“好一个教化,连暴元鞑虏也被教化了,让这些豺狼终于披上了一张人皮。”一个脸型瘦削的年轻人轻轻哼了一声,然后接言了一句。
这一句话却像滚油锅里丢进了一滴水,顿时就炸开了,十几个学子开始纷纷指责那瘦削男子的狂妄之言。
“暴元鞑虏习理学之德,知廉耻,遵三纲五常,有何不可?以禽兽而转斯文,当然是我理学教化之功。圣人之志,当德泽天下,倡审察名号,举教化万民,我理学劝化鞑虏,岂不大善?”
“豺狼披上一层人皮却还是豺狼,鞑虏奉了程朱理学,遵了三纲五常,我们就要安心做他们的奴隶了吗?”瘦削在群言汹涌之时却毫不示弱,一出言就命中要害,使得众学士一时都哑了言。
能来参加国考科举,就是认同了刘浩然江南政权,那也必须认同刘浩然提出的“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政治纲领,如此就陷入了一个两难境界。
那位白净无须书生也是机灵的人,话锋一转对答道:“暴元鞑虏终究是外敌,他就算是被德化也要还我中华神器,如是不愿退回漠外,也要顺我中华民意,奉天朝正朔,安心据臣,潜心受教。”
他几句话就将理学德化与驱逐鞑虏拉扯开,所以有点勉强,但是也说得言正义直,旁边的学子在此鼓舞之下,都理直气壮起来,并纷纷出言附和道。
“就是如此,我们理学秉承天理之道,行大善之事,能德化禽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禽兽之类,岂能一时二刻便能反正附善?”
“那你们可以继续德化鞑虏,一百年不行,两百年总行吧,我们中华之士就继续当奴隶等着你们把鞑虏德化好。”瘦削书生有点嘴尖牙厉,死咬着对方最引以为傲的“德化”,几句话就把白净无须书生顶得死死的。
“叶淙尧,你简直是狡辩!”白净无须书生终于动怒!
“我怎么狡辩了?你对禽兽豺狼读上一万遍《大学中庸章句》,它们就能改为不吃人了吗?教化不过对知理持礼、本『性』未泯之人,对付豺狼还是要靠实力,而实力从何而来,工商耳。”
“叶淙尧,你就不要鼓吹你们永嘉学派功利那一套,你们那一套简直就是对圣人之言的一种侮辱。”
“内圣外王、经世致用,我们也是秉承圣人一脉,就许你们发圣人之言,叙圣人之志,别人就不行吗?这难道不是党同伐异,唯我自大吧?如此胸襟,安能处之庙堂?”
“我们理学秉承天理,行圣人之道,岂能是尔等妄言轻语所能比,我们程朱理学不能居于庙堂,难道你们永嘉之学就能吗?”关系到师门,当然火『药』味就浓了。
“我永嘉之学不求居于庙堂,只求造福社稷。不过谁居于庙堂都可以,就是程朱之学不行!”
“为什么?”白净无须书生不由跳了起来。
“暴元所用,必有所图,鞑虏所重,必有所害。”叶淙尧冷冷地说了一句,白净无须书生脸『色』又红转白,又由白转青,最后一言不发地悻悻坐下来,而刚才还热闹万分的楼层一下子冷静下来。
冯国用还在那里品尝着桌上的菜肴,仿佛刚才的那场争论与他毫无干系,陈遇笑了笑,却默不作声,学着冯国用在那里品菜,潘庭坚的脸『色』变了变,悄悄地看了一眼刘浩然,却没有开口,也继续保持沉默。
刘浩然的心里却一声长叹,因为叶淙尧说得这句话是自己说的,而且是当着江南行省众多重臣说的,想不到居然会传到了学子们之中。
当江南开科举之风传遍天下时,河南名儒胡从宪赶到了江宁,以奉献程颢亲笔书录《易经》为由求见刘浩然,得到了刘浩然的热情招待,并授为行省博士。胡从宪安居江宁之后,便与宋濂等人交好,并极力推崇程朱理学,拉拢众多理学文人名士联名要求江南将程朱理学定为官学,并依元庭例,科举内容以程朱理学思想为主,也就是以程朱理学的标准来判题,却招到了刘浩然宛然拒绝。
但是这位胡老夫子不依不饶,依然纠缠不休,结果把刘浩然惹出火来,前不久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甩了那句“暴元所用,必有所图,鞑虏所重,必有所害。”把问题提到了民族大义、夷夏之防上,一下子让胡从宪无话可说。这位河南老夫子终于明白了,在刘浩然的心里,程朱理学是鞑虏用来拉拢、收买中华士子的工具,是为暴元歌功颂德的把戏。而天下人都知道,刘浩然是出了名的反元死硬分子,这程朱理学在元廷那里吃香,自然要被刘浩然所轻视。
胡从宪意识到问题所在,但是不死心的他转为想其它办法,毕竟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中,程朱理学是主流,他大可以从长计议,这次科举国考也被他和一帮理学狂热分子视为一个机会。
争论很快就平息了,白净无须书生那一帮人觉得无趣,不一会就走了,叶淙尧等几个人也随即离开了。
“中行先生,叔闻先生,你们谁知道叶淙尧此人的底细?”刘浩然突然开口问道。
“回老爷,我略知一二。”陈遇轻声答道,市野之中,不便称呼刘浩然的官职。
“叶淙尧是前宋水心先生的三世孙。”
“哦。”
看到刘浩然颇有兴趣,陈遇便继续说下去。
“水心先生,即叶适叶公,字正则,历仕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水心先生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另外水心先生注重治史,考求历朝成败兴亡的道理和典章制度沿革兴废,寻求经世致用之道。他是永嘉之学的翘首,在前宋与朱学、陆学三足鼎立,后来暴元南侵,永嘉之学便衰落下去,仅延续在温州路一带。叶淙尧秉承的是家学,也是现存永嘉之学的领军之人。”
“中行先生了解地很仔细。”刘浩然点点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