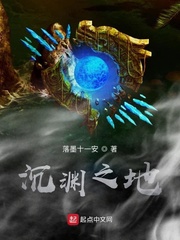故旧知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江南的夜风,缱绻温柔。
谷家院后的谷仓内,昙笙不知不觉睡着了,取下了帷笠的臻首不自知靠在了身边披着蓑衣的宽厚肩膀上,越靠越沉。
林蓑鼻间能闻到昙花一现的馨香。他伸出另一边手想推醒少女,听得她轻匀的鼻息,又有些不忍。
“其实你不用叫醒这姑娘,要我说,以那位沈家师姐的性格,肯定不会介意。”传来徐行调侃的声音。
“胡说些甚么?!”林蓑立时不满道。
“啧啧,你看,急了。对了,我说林蓑,你没发现这几年,你都有意无意躲着吴州走,这次进来,说不定冥冥中,你还得谢谢你肩上这小娘子咧。”
林蓑挤了个难看的笑道:“就算要谢也应该是谢骨盦里的谷自生吧?”
“就一盦中主顾有甚么好谢的。不过说起来,你腰上另一副盦,背得是不是也太久了,差不多得了,找个契机就取下了罢,懂你的人自是懂你,不懂你的人得说你矫情较真。”徐行望了望渐渐升高的满月,对搭档碎碎念道:“老是负着千斤行走,不累得紧么,我就受不了。”
林蓑沉吟不语,想要开口,心中泛起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吐不出一个字来。
还是徐行寻思可能刚才一番话说得不甚好听,先开口打破了沉默:“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说,这件事完了,应该有几日时间。要不去看一看沈家师姐?”
“嗯……好…”林蓑的声音细得几不可闻。
徐行在谷垛后忽然坐直身来,说道:“欸,对了,不如让这小娘子留在这谷仓里睡吧,我俩换个地方,也好打架不是。”
“不成,万一她醒了看不着人怎办?”
“哎哟,你还真当人家是三岁女娃,人说不准比你当年都沉稳多了,你还记得你当年什么德性。得了,她在这里也好藏身,留张字条让她安心等着不就成了!”说罢徐行便从怀内掏出了传信用的字条矾块,写了起来。
“也是,便说让他在这谷仓里藏好候我们回来。”
一对搭档安顿好熟睡的昙笙后,便离开谷仓。一左一右纵上谷家房顶伏好,正当此时,田间小路上出现一胖两瘦三个身影,正打着一双灯笼鬼祟而来,灯笼上两个楷字,一田,一农。
谷家屋内只有一盏残烛,农筠竹怔怔地凝视着案上的骨灰盦,没被散发遮住的半边脸上毫无表情,只剩干枯的嘴唇间不时挤出的几句唱词,便是这屋内唯一的生人气息。
“清泪泡罗巾,各自消魂,一江离恨恰平分。”
门外的胖绅先来到门槛处,却不敢推门进去,悄声招呼身后两个瘦绅:“你们俩,快些,快些,瘆人得紧。”
“催甚么催?!”其中一个瘦绅一边啐道一边扯起袍子小跑跟上,另一个则低头不语,脚步沉重地随在最后。
“你说你侄女不会是死了吧,怎一点人声气都没。”
“我如何知道,进去看看。”一巴掌把胖绅推个踉跄,险些跌进屋内。
唱词戛然而止,一声低得几不可闻的女声切切传来:“都进来罢。”
三人听闻一阵惊颤,慌张过后把原本跟在最后的瘦绅推上前去。
那瘦绅不敢抬头,拱手颤巍道:“女儿,这两日可好,父亲来看你了。”
“托父亲的福,好的很,还有两位长辈的,能有今日,全仗你们照顾。”女声应道,最后“照顾”二字,带着切齿之声。
“这…为父也不想如此,实为形势所迫…”
听得瘦绅的话说得支支吾吾,胖绅把心一横,一脚把瘦绅蹬到一边,恶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她废什么话,农筠竹你听着,你那薄命夫君是我们雇人做掉的,谁让他想逃跑。怎么地?不想随你相公一起上路,就识相些把胚米的稻种交出来,或是告知我哪一块是胚米种田。”
农筠竹放声大笑,似是听到了这一生听过最好笑的话,笑得浑身乱颤,笑得前仰后合,笑得墙上烛影颠来簸去:“你等觉得,我还会怕死吗?哈哈哈哈”
“管你怕不怕,今天你非说不可!”说罢便取出一捆麻绳,将农筠竹拽倒在地,双手双足紧紧捆缚。
“你说不说,不说,我用绳笞打了。”
“勿打,勿打,先商量,先商量。”农郁仁急急忙抢上前来,扯住田万顷衣袖哀求道:“女儿,你说罢,你只要说了,就不用受苦了”
女人犹在狂笑,连眼角,也笑出了泪。
“你起来,现在来装什么慈父,讨要好处时声音最大的如何是你!”田万顷和农益仁把农郁仁踢到一旁,齐齐举起绳鞭道:“筠竹,你不要怪我们,怪就怪你那夫君太不识抬举,若是他逃跑那日,肯乖乖把胚米稻种之事和盘托出,也不必落得个身死异地的下场。最后问你一次,那稻种何在?”
林蓑此刻在檐后看得一清二楚,他也明白了农筠竹白日里拉扯衣袖要掩盖的究竟是什么,若是多年前,檐下的鞭声有几分急,他想纵下去的冲动便有几分,可无数的生死冷暖见惯,加上远处徐行所打的眼色告诉他,谁此时现身,谁便先成了捕蝉的螳螂。
他只是用力按住归渔剑,按捺住鞘内的涌流。
农筠竹的笑声夹杂着呻吟,荡在界桥南岸的夜色中,有如鬼嚎。
没多久,许是两个富绅打累了,俯下身来气喘吁吁:“骨头真够硬的,看来绳子是不够好使。”
农筠竹一双仿佛要滴出血的瞳孔直盯在眼前三个身影上,蔑道:“怎停了,继续啊,我的义父,我的叔叔,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