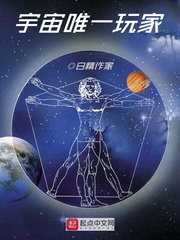丁染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见她不答,他便如此认为,将那对母子迁入府中,确是令她伤了心。暄当即走上前来,也同她一般坐在脚踏上。
阿七几不可察的朝远处挪了挪身子。暄却并不在意,将手轻掸了掸衣摆下缘的水渍,似是随口说道:“许久不曾骑马。前些时日柯什王使自西炎带来的烈马,如今已调教的甚是乖觉,不几日便要牵去围场供圣上选看。前次围猎不曾尽兴,此番我亲自带你去吧。”见那阿七竟是无动于衷,索性又笑道,“西炎人亦是驭马的好手,可去长长见识。再有,西炎九王子幽酋沙彻生性狂傲,极不入我的眼,今次见了此人,你替我好好煞一煞他的锐气。”
阿七自知身无所长,如若不是比试斗嘴互骂,便也唯有比试骑术——心中索然,仍旧不应。
暄并不死心,在她身边絮絮又道:“还记得你我初见之地么?前几日往西陵去,又路过那处桃林——”见阿七别过脸去,知她心生触动,便接笑道,“你可知当日启程北上之时,弥须特为卜了一卦,道与隋远‘朔日不可西行’,我却命人绕过大半个城郭,专拣了西门出城——不早不晚,便遇着你。”
阿七在旁听得暗自咬牙,却又无可奈何——恨自己明知这男子巧舌如簧,却每每被他三言两语便哄的回心转意——红了脸再开口时,话音中全然没了清冷,倒多出几分娇嗔:“记不得了!不许再说!”
见已是水到渠成,暄笑着将她揽进怀里,“还未完呢,且听我讲——当日怪我小瞧了弥须,他的卦,竟俱是准的——临去时他还道与我,‘莫近极洼之地’。待我出了雁关,闲来无事坐在车中寻思,北祁放眼一望皆是平的,这‘极洼之地’还真不易寻。可巧有一日将过玉镜,茅塞顿开!都道这玉镜乃是祁地一处海眼,与瀚海相接,可随月相生汐,不恰是极洼之地么?当晚便自宿营处折返,往镜湖中游过一遭,便猎回一条笨狐狸——”一面说着,唇角已触上她的耳垂,嗓音渐次低了下去。
唇边带着一抹轻笑,好似悄然在飞蛾周身结网的园蛛,缓缓将她收入网中,又剥茧抽丝般,细细散开她的鬓发与衣裙。。。。。。。雨声骤急骤缓,一下下打在她耳畔,始终不曾止息。。。。。。终待这番雨势过去,两手抵在他赤裸的胸前,指下所覆的,正是他心口处的疤痕,带着凝涸的血色,三翼状,看得她暗自心惊——由这箭疤便不难想见,此种箭簇应为玉钢所制,矢锋必呈三棱形,铸有极细极深的血槽,利可透甲——燕初口中的埈川寇患,不是由衍西饥佞流民聚合而成?却为何有如此精良的兵械?
指尖一次次自他心口划过,终是被浅睡初醒的男子一把扯过,紧紧攥于手心。
窗外已是雨住云收,酉时未至,尚有轻浅暮色斜斜透过窗棂——阿七微微侧过脸颊,避开欺近自己耳畔的男子,轻声问他:“你可曾留意伤你的箭簇?”
“如何?”暄懒懒应着,指端绕了一绺她散落在枕边的长发,“你却见过?”
她非但亲眼见过,且曾听继沧提及,第一位铸成此箭的,是一名乐浪匠人——
阿七答非所问:“万斤铁砂与木炭一起投入熔炉,三日三夜始得,是为玉钢。技艺娴熟的匠人,取玉钢摔折,择其易碎者,为刃为锋,可轻易刺透铁甲链甲。。。。。。此法不为中土匠人所知,出自乐浪海东。。。。。。”
暄静静听着,看似不为所动,心中却绝不似面上这般平静——这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惑,如若她肯吐露,自是省却他诸多麻烦;若她不肯,他亦曾对她说过——绝不多问一句。
而此时阿七将面颊埋在他胸前,似在等他发问,却又怕他问——若他开口问时,自己可会答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种种前事尽数向他道来?即便恩主已将她舍弃,她便可行此背信之举么?
云七,事到如今,你究竟该如何自处?
碧芷园。
薄雨初收,遍野黄栌,红叶胜火。
此刻望春阁中坐满了宫装女子,正纷纷望着几名略显忙乱的粉衣宫娥攀上楼阁。未待那几人进来阁中,先便见着小小一个身影跌跌撞撞攀爬上来,倒将一众婢女撇在后头。
粉雕玉琢的小人儿,生的真如雪团一般,又是一身石榴红小裤小袄,啃着拇指,咯咯笑着打量众人——众人瞧着俱是喜不自禁,长公主亦忘了责骂忙忙追来的乳母婢女,只向她们笑问:“谁是跟着的人?”
内中便有一名年轻妇人,乃是司徒太后亲选的乳母,身份与别个不同,裣衽施礼道:“奴婢甄氏,见过长公主殿下。”
沐阳公主含笑点头。那甄氏便将小人儿拉至身边,取了帕子拭他额上的汗。
见那长公主手中亦是执了帕子,掩在唇边兀自笑得何不拢嘴,在旁一名年长些的宫妇便也笑道:“都说儿肖父,瞧这孩子恁般淘气,他父王当年便是个一顶一顽劣的,如今瞧着怕也不及他!”
“小娃娃哪有不如此的,便是他父王,当年且有的淘气呢,非但自个儿淘,还领着年长他许多的小叔叔们淘——姐姐常年在宫里,听得不多,”沐阳公主笑指了指下首陪坐的义平侯之妻田氏,“只管问问她,便可知了!”
田氏便讪讪陪笑道:“殿下回回尽拿臣妾取笑,再要提时,臣妾可要羞死了——”说得众人一齐笑了。
长公主因又问那甄氏:“如何跑得这样一头汗?”
一名宫娥便跪下回道:“方才在后山温水池子里,与几位公侯家的小世子小公子们玩水,这才扑的一头汗。将擦干了,又急急的跑上来——”
长公主不禁冷下脸来:“才这样小一个孩子,你们一群人竟不知好生领着么?”
甄氏赶忙跟着跪了:“翀公子年岁虽小,却天资不凡,方才挣开奴婢的手,几位公公都不曾拦住他。。。。。。便是在后山玩水时,几位小世子还年长些,身量亦足,倒被翀公子欺负的哭了好几位。。。。。。”一面说着,一不留神那小人儿已爬上就近一张矮几,伸出小手便将硕大一只鎏金酒壶攀住,内中装的却是将将烫好的桂花酒,唬得众人赶忙抢下——
小人儿将旁人闹的手忙脚乱,自个儿却咯咯直笑,叫人恨也不是爱也不是——正没个开交,只听台阶下一声暴喝:“赵元翀!给我滚过来!”
阁中坐的俱是内外命妇,敢如此喧哗者,不消想便知是何人——只见一袭明黄骑装的皇长女幼箴,手里兀自执了马鞭,正大步踏上石阶,口中恨恨道:“趁你父王不在,让我好好调教调教——”
幼箴身后跟了一名宫装女官,乃是司徒文琪;另有一名鹅黄衫裙的女子,正是潘氏景荣——这二人倒不理会忿忿不平的幼箴,只浅浅笑着,上前来与众人一一见礼。
沐阳公主一手携了女儿,一手携了文琪,叫她俩一左一右挨了自己坐下,又笑向幼箴道:“你不是随那些西炎女往秋坪骑马去么?元翀又如何招惹了你?”
此时赵元翀被甄氏自矮几上抱下,又遥遥冲幼箴摆着小手,许是在他眼中,幼箴手里明晃晃的织金长鞭与那鎏金壶嘴无甚区别。
幼箴上前正欲揪他的小耳朵,倒被他先一步抢着了鞭梢,抓起便往口里塞。
沐阳公主忙吩咐甄氏道:“快抱开些——”幼箴扯过鞭梢,顺手向元翀粉嫩嫩的额上弹了记爆栗,这才作罢。
上首肖妃便向幼箴笑道:“公主也下得去手!真跟个孩子似的——还不快过来坐下。你姑母请了温淑人稍后过来叙话,你们也瞧瞧人家隋将军府上的几位女孩儿,虽说是将门之女,倒个个贞静娴淑。”
幼箴嘴角一撇,向肖妃身边坐了,便听席中有人问道:“隋府的三位姑娘倒是许久未见,今日可都来么?”
青宫肃夫人亦在座中,此时便笑的有些意味深长:“不止呢,倒还多着一位——如今有一位寄住在他们府上的姑娘,据说还是苏太妃的族亲。”
司徒文琪一听“苏”字,不觉便沉下脸来,又怕被人瞧出,忙取过茶盏,低头佯装饮茶。
好在苏岑拒与司徒氏结亲一事,在座知悉的并不多,却不知何故,今日这肃氏似是有意招惹司徒文琪这太后跟前的红人,当下又不紧不慢道:“司徒女史竟不知么?听闻这位姑娘倒是身世堪怜的一个人儿呢。无父无母,进京投奔了苏将军,终归是不甚妥当;如今寄在隋家,时日亦不算多。对了,前些时候宸郡王要三书六礼聘进门的,莫不正是她么?怎的过了这许久了,宫里也还没个准音儿呢——”
此语一出,非但文琪、景荣心中有异,长公主并在座的肖妃、肖瓒之妻姚氏,亦是个个心生不快——肃氏并不在意自己一番话得罪了一圈儿人,只闲闲的取了茶,端在手中撇着浮沫。
一时席间倒静了一静。见那沐阳公主无意开罪东宫,肖妃与姚氏亦只是冷了脸——司徒文琪虽是未嫁之身,议之不妥,却有熙和宫女史的身份,便笑了一笑,道:“夫人有所不知,如今这些年轻王公侯爷里头,太后最看中的便是宸郡王,他的婚事,必得是太后亲允了才作数的。”文琪一面说着,亦不等肃氏接话,又笑向景荣道,“方才公主说此番九王子带入京中的西炎马匹,性子最烈的,却叫什么来着?”
景荣正满腹心事,此时微微一怔。倒是幼箴早在一旁云里雾里听得不耐烦,此时总算来了兴致,便忙忙的替景荣答道:“‘朔风’么,比之先时送去祁地那匹,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说多少回你俩也记不得!”
“谁说记不得了?”景荣亦晃过神来,浅浅笑道,“朔为水,水之色,黑也;迅如风——”
“莫说这些,”幼箴笑道,“另有一匹,和朔风不相上下的,又叫什么?”
“一时倒忘了。。。。。。”文琪思忖道,“叫。。。。。。瑞玛!这西炎人取的名字,果然拗口!”
“古书中称其为‘麢’的,像羊又像鹿,”景荣点头笑道,“兼之皮毛俱为银色,西炎语读来,便叫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