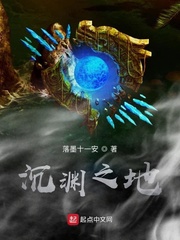尹四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员外一听兀自一慌,心中暗想:“难不成是他们寻了来?”
但仔细一琢磨也不对,平顶山离的此处有一千多里地,此间又离得云阳宗如此之近,在这穷乡僻壤的消息闭塞,平顶山的师门要来早便来了,缘何又等了这十多年?
想到了此处,胖员外也便安下了心来,只要不是平顶山的人到了自是无碍。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退下去,管家你自将来人打发了,休得惊动了此间客人“。
徐大先生放下了酒杯,但此时不知发生了何事,倒也不好唐突了。
但见这管家方自出得厅堂,便已被人又打飞了进来,趴在地上直哎吆,已然爬不起来。
玄清观,自八卦台议事后,各自散去,一平也便只待次日前去领罚。
次日,一平自去领杖,到得静室,尘方将由门人抬了出来,已然是打的皮开肉绽,兀自趴在木架上唉吆吆的叫个不停,但见得一平也来受刑,竟还不忘发出阴恻恻的笑声。
尘方咬牙阴笑道:“你这挨千刀的小贼,先叫你尝尝这杖刑是如何滋味,待道爷伤好了定由得你好受..哎吆疼杀道爷,你们这帮臭小子怎的还不去取了金疮药来,哎吆..哎吆怎么下手如此歹毒。”
说着自由门人抬着去了。
一平却兀自好笑:”大师伯,您自是万金之躯,我贱人一个,皮糙肉厚挨这几板子自是受的,不牢您老人家操心。”说完还之以大笑。
自是有一干人等,跟了过来看一平行杖刑,已经好多年没人受的如此多杖,一个不好是要被生生打死的。
到了行刑之地,一平自己爬到了台上,由得杂役施刑。
施刑的不是玄清弟子,而是膳房的杂役。这也有些道理,毕竟师兄弟行刑,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怕要伤了情分。
这杂役一平自也识的,便是菜地里的李四,这人生的人高马大,虎头虎脑的。
为人耿直的很,说话有些结巴。但却有的一把子好气力,平日里二百多斤的大石碾子扛起来便走。
一平整日里去膳房找老牛皮厮混,与李四自然相熟。
一见是此人刑杖,也是暗自苦笑。
一平口上虽是嘴硬,但心里却想:“他姥姥的,今日看来老子当真是不死也得去了半条小命。”
李四自是也识得一平,平日里两人也谈的来,一见是他,也是怪难为情。
一平看出了李四顾忌,便道:“你这大老爷们,怎的今日便像个娘们,赶紧的给小爷挠痒,打的好了,小爷请你吃酒。”
李四面皮微红,也不说话,甩开膀子便开打,啪,啪,啪,端的是杖杖到肉。
就这三下,第一下一平便已冒了冷汗,浑身直打颤,但却兀自大喝:“李四你今日没吃饭是怎地,竟给小爷挠痒?”
起初还有尘方的弟子,在下面看着,生怕李四偷工减料。
有些幸灾乐祸的在交头接耳道:“哼,看这小子能横到几时,十几杖下去定叫他哭爹喊娘。”
此时一平抬头四下打量,却见尘清不在当场,还暗自苦笑失落了一把。
心想:“定是小师姑不忍瞧我受刑,但此时没来,自是见不到我这英雄气概了,可惜的紧。”
还没想完,就听啪的一声又是一杖落下,一平明显的感觉到这一下重了许多,疼得他已是冷汗直冒。
心中暗气,我怎的忘了李四这憨货一根弦,老子自撑英雄,你怎的还真使上了浑身的气力。
‘啪…啪…啪’行杖之声不绝于耳,再往后一平已经没得心思再去胡思乱想了,这会已经疼的是要支持不住了。
但又瞧见台下尘方弟子,有几人竟向是在耻笑他一般,好像在说酿你小子也要哭爹喊娘了吧。
一平的倔劲上来,老子偏是不喊,紧咬牙关兀自一声不发。
沈家庄,沈府厅堂门外果真闯进两人,两人头戴斗笠,身着布衣,其中一人手持的是丈长金丝鞭,一人用的是一把鱼龙短剑。
二人进了堂内率先看到的便是徐大先生,徐大先生见这二人虽是男装打扮,却是女儿身。
当时便站起身来,立于一旁。
身形稍矮的一人,看了一眼徐大先生,便火冲三丈。
“好啊,原来你与你那宝贝闺女竟和这些个挨千刀的贼人是一伙的,今日就是杀了你们这般狗贼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了!”来人正是尹青竹与子陌二人。
昨日青竹与子陌将那师爷打走,本是高兴的紧,自觉为那一家三口出了这一口恶气。
谁料那妇人竟瘫坐在地,骇的爬不起来。
子陌见他们竟这般害怕,才想到其中缘由,气是出了,但若我们走了,留下这一家三口,那干恶人再来滋事岂不是苦了他们,想到此处她也是自觉方才是鲁莽了。
子陌遂与姑姑商议,如不若让这一家三口去的穷桑城住下,便不再怕这些人再来滋事了,两人一拍即合,子陌即将这法子说与这牧童一家人听。
这牧童一家自是听过云阳宗穷桑城的,但却好像不愿离开此处,像有难言之隐。
这一家人本穷的身无分文,只能靠着此处的一亩三分地讨口饭吃,牧童则为那沈官人家里放牛来冲抵人头税,就是去了云阳宗也是活不下去的。
子陌看透这一家人的顾虑,便说拿纸笔来,我们在云阳有做生意的亲戚,我写一封书信你们带了去,便在我那亲戚家里干些零活,也能度日的。
这一家三口听后自是喜出望外,连忙跪下磕头谢恩但还有一事需求恩人相助。
说着一家人又自磕头,子陌同青竹赶忙相搀。
从妇人口中得知,原来此处叫沈家庄,之前的沈家地主待他们这些佃农还是不错,但十来年前突的来了一伙人,竟占了沈家的田地。
沈家之人去报官府也是无用,这伙人来头甚大,自此便同官府蛇鼠一窝。
官府拿了好处怎还会在乎我们这些个贱农的死活,任得那伙贼人欺压我们,直将我们当做牛马来用。
过的几年这里的人越走多,过不下去的都去投奔了亲友。
剩下的都是我们这些个无路可走,和庄子里那些个能拍马溜须的买卖人。.uu&#
;
&#
;h.
“那大嫂,童儿和大哥的伤是?“子陌问道。
说到此处,那妇人竟哭了起来:”那伙人见庄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便常年看起了我们,怕我们都跑光了。
我这娃娃五岁那年便被他们唤去放牛,娃娃小怎的能放的了牛,结果牛跑的丢了。
他们..他们便将我这娃娃的舌头给..给割了去了,我那般小的娃…我们对他不起啊。”
言至此时,那妇人已经嚎啕大哭。
子陌听的也是义愤填膺:“那你们怎的不走,就是出去要饭也是要比这般苟活强的。”
说着子陌竟颇为恼火,她气的是那般贼人的歹毒,气的是这一家三口的懦弱,为何不离开此地,一时间又生气又是同情。
“恩人,您怎知我们便不想着离开这里,便是饿死在了外面也不想再这般的活着,但自曾庄子里的人越来越少,那般贼人便控住了我们。
都走了谁又能来种地交粮,两年前我们也曾逃过,但被抓了回来,这庄子里逃跑的人都被抓了回来,一家总得有一个被割了舌头,留的一个会说话之人。
孩子他爹为了..为了..我,也被那班人给割了舌头,这是让我们有官不能告,有苦不能言。
如不是恩人愿助我们,我们又怎能走得了。”
听得这妇人将这一番血泪过往娓娓道来,子陌方自明白,这里的百姓就是如牛马一般被人圈养着。
她紧攥双拳,暗自咬牙切齿,打定了主意,此番若不能将这股贼人尽数除去,还走的什么江湖,行的哪般的侠义!